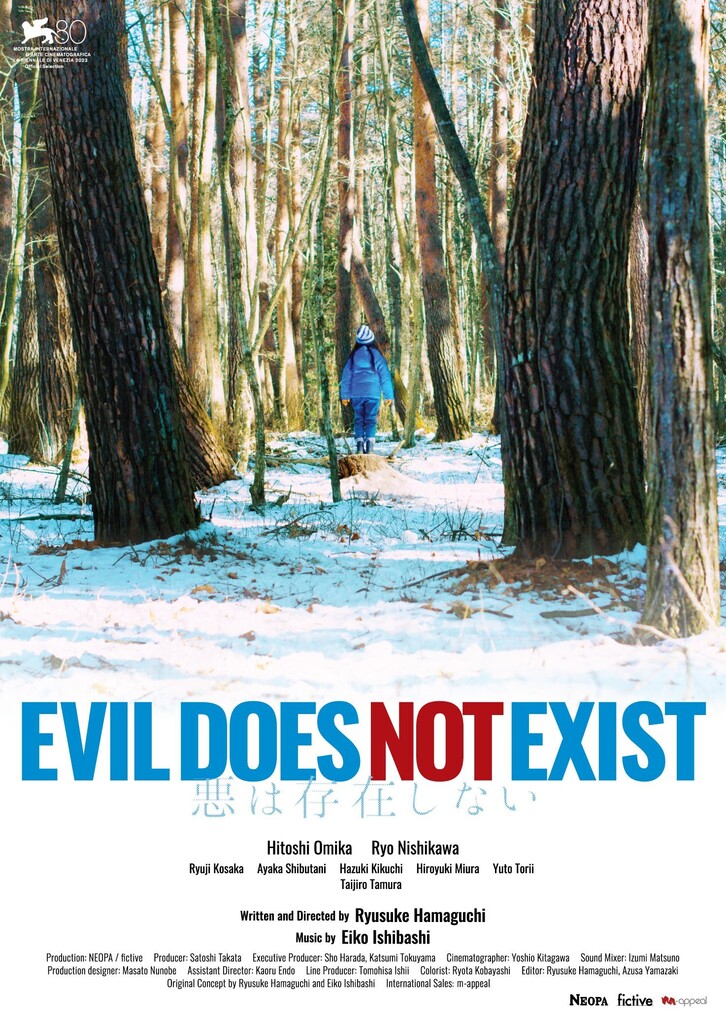
作文青必去追捧的文化吉祥物口介,新作《邪之境》有像要深入去打文青那些借文化、、保、自然等包享至上及消主信念的意。影先心自然的原居民豪露破自然生的,及後反思即使已用於自然珍惜地方的居民也只是外者,在「天地不仁,以物狗」的邪面前,有比高尚,都在消自然。
消有比邪,和提倡保及人生那些概念其都一,只是人了某目的生出的口而已。正如不管是冬店用地泉水做,用掉落的羽毛做器,是巧用大伐木,在大自然面前,同邪。情就如去文青咖啡店不比去大排雅,而去山品茶甚至耕的人也不一定比去文青咖啡店的人更高尚及懂得自然,甚至真的自然共生的人,如同巧,也有更值得致敬。真正邪的只有死亡,人所有的行都只在自以是地分享受、庸俗、文青、高、性,但只要人在活,一切都是消主的物,都以不同程度破自然。
令我想起狎井守用了九年作《攻》集,其副也是「邪」,但英文便更或更具佛教味道Innocence。也不知是有意意,像是回「物狗」一,影以「人偶」和「狗」作影片主,探人的魂究竟是什,甚至及人是否存在於世,已是一破或罪的。然它《邪之境》容完全不一,的焦各,但我二者思考的似乎是一致的。就像迦最初提出的道一,我是否做什也只能自然立,人(肉)是否必然被排除於「邪」之外?如果人也是自然一部分,人建立的文明又是否自然的一部分?再是,捕捉美自然,配上大量美音的演及影,又是不是消?影最後的局,就代表正地回自然?如果野生生物可以了保人及自己而反,什人就要保自己人而有罪感?就叫自然共生?就叫做敬拜邪?影有答案,最後只是映照着如同最初是的仰望天的,慨生命。
比起,我更向岩明均《寄生》中於存在主的述,提及人只能以人的思看世界的。即使主角新一人有格去其他生物的生存利,但作渺小的存在,他保自己及人,最「行」死已反抗能力的寄生生物,也是法。不管人作自然的破者或共存者,我都可能地邪,而可逃避地只能以人的角度,以不同程度的判看待自然,以及也用自我的基看待些判,包括女的(看似文明但在物面前可能是另一意思),巧的行,豪露的位代表的心理,作,助片的自然保育位,乃至的想法也如是。
倘若,我能抽身於影的美及感,回看日本文明如何地回土地及文化,再比香港所的保保育,便似乎香港在大氛下入土地的交流及也未有。所以,如果,是不只品味文化及文青生活,沉浸於尚及影美,而是能引人思考及感情的影,那它就是好影了。
xxxxxxxxxx
另外,了天再回想最後的局,也可能有另一或更的解,原因是解的,之前的所有及喻就成立了,那是巧等於受的鹿。面上,鹿就有攻女,而是女中了。以致巧崩地旁的「入侵者」,然而他也知道不方事,而回理智及悲。然而,的法,就完全地陷「半箭的鹿」,那一次的喻,而之前的所有於自然人的,全推向是是巧於被入侵的忍耐上,而藏的暴力意象就越明了。
如何,巧作人自然的中介人,他抵了自然,原居者,甚至外者的力,努力地去念求,在失去女一事上情感爆,在忠於自然法及人性欲念之扎,面也不是,只留下悲哀。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