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生命,是量的生死程之中,一小小的片段而已;凡夫在一生一生的生死流中,是在造,又受苦下去,因不懂得要如何去修行、去惑!而四即苦、苦集、苦和苦道,苦、集、和道,即是佛陀教的基本修持法。
三界的苦有八,即是1.生、2.老、3.病、4.死、5.、6.怨憎、7.求不得、8.五—色受想行等等盛苦。
八苦之中,欲界的生只能感受到前面的七苦,到了色界及色界,才能感受到第八苦(五盛)中的行所招致的苦。
第八苦括了前面的七苦,也即是前七苦的。五亦即五,此苦有二:1.就苦而言,人皆各具五,因而苦盛。2.由於具有五之器的身心世界,盛苦,故名五苦。
五,在《阿含》及《阿磨》,作五取。何被五取?因五的生,就是由於取、等,故五取;五常於,五能生起,故名五取。
因有,故生五之象;因有五,故生之著;互相取,互相依存,彼此。娑婆世界,不地由五取,由生起五,不地生,就是三界中的生受苦。
而此三界五取不盛,就有生,就有苦,就有世,就有三界。《心》云:「自在菩,行深般若波蜜多,照五皆空,度一切苦厄。」透修行而般若智慧的目的,就是要照「五皆空」,就是要五取的盛之苦而得到解。
四法印就是苦及苦的道理,那就是:行(行)常、法我,有受皆苦、涅寂(空),言之即是常、我、苦、空。若不悟行常,就是苦;若已悟行常,常即是空,空即是我。若就常、空、我的三相而言,是三法印,若加上苦相,即四法印,也即是苦的四相。若悟此苦的四相,就能通佛法,一切苦而得涅。
若愚生的立看,苦就是苦。若以佛的智慧看,行常,苦亦是常,苦既是常,也即是空、也是我的,既已我,那有什苦呢? 原因在於已明明知道常、我、苦、空,但深陷常、我、苦、空法自拔,明又愚而且不放下,自己一直苦苦苦地下去。/span>
「因果海,果因源」,多半的人只能看到一生,不相信生命是在去量劫之前,就一次一次的有了。「果」有苦有,生於幸的事,很傲的是自己明、好;遇到困,就怨天尤人地得很倒楣。事上受苦享,都是有前因後果的,有的是在量劫以所造的,累到一生而得到了果。
根本衍生出的,是名枝末,有量。根本主要的分成、、、慢、疑、的六大,枝末即六根本之眷,由根本而生枝末;也就是,只要根本消除了,枝末自然消失不起。如果不修道,永在,有就持造。
六根本所生的枝末有量,所以八四千,也就是有八四千解道法的障;因此,要修八四千法,治八四千。不,八四千在是太多了,我只要先抓住思二惑的六根本,做治的功夫就可以了。
以「思」,能根本意志,而形成身、口、意三。有表(作)及表(作)。造的性,有三分法:1)善、、非善非的,2)黑及白,3)及清。
「表」有身、口、意三型,那就是身口意、意身口、意口身。只用「意」,就是叫「思」,意跟口或是身同行,叫做「思已」。思然是有表出的「表」,但是它形成一力量,力量之力。
譬如你不地想要人,的力量推,你就形成向於人的行。因此,然是表或思,事上有做什事,但是,是要悔。
佛:「南浮提的生,心念,非是,非是罪。」南浮提就是生所住的世,凡夫生的心念,都是自私自利的,因此而造,若不及悔也就造苦的因了。
自己若不知道苦因是出於自作,在受苦,就苦上加苦,而既知苦果自苦因,受苦之,心境也平,不以苦,此,你就已苦因苦果得到解。先要用修道的方法,除苦的事,由修道而苦,也就是只要不再造作苦的因,苦的果也自然有了。
在真正解了苦及苦之象,又已知道苦果是由於造了苦因的,受苦之,心境也相平而甘之如,不以苦了。如不知道苦因是出於自作,就不意接受苦果,在受苦的候,就成了苦上加苦。
世任何的象,都是因和合而生的,任何一象,只要另外加了一因,那象就改,得或好或;或者得更,或者得更破,乃至得有了。但最的事物,在世法中,是未曾出的,因到最,上已始衰退。
因此任何一事,任何一象,都是因生,因。因而生的化,是有一定的、有永恒的、有不的,它的性都著新的因而起,因此法的自性即是空性。
若十二因的成就及生成就而言,即知苦果及苦因何物;若由及生逆及成就,出三界、五、入涅。(十二因是指生命程中的流象,明、行、、名色、六入、、受、、取、有、生、老死等十二段。)
逆、是什呢?逆是,是有。
「」是,明所以有行;行,所以有;,所以有名色;名色,所以有六入;六入,所以有;,所以有受;受,所以有;,所以有取;取,所以有有;有,所以有生;生,所以有老死。知道之後,就得生死之苦是怎的,生命受苦的原因是怎一回事。
「逆」是明起,因明,故行亦,行故亦,故名色亦,名色故六入亦,六入故亦,故受亦,受故亦,故取亦,取故有亦,有故生亦,生故老死亦。
此逆、生二,亦即《阿含》所:「此生故彼生,大苦聚集;此故彼,大苦聚」。
如何使得逆成就呢?首先由明著手。明是有智慧、知不正,所以起心造。八正道中的第一目是正,乃是要以正指人,使之我的智慧,以智慧之明破的明,明若,乃至老死也。生已,即涅而登阿位。
,解生死,即涅,涅就是寂。不,是寂,不起,是。根原始的佛法,涅有:
<1>有涅:即是在生中之苦得解,不情,不受境。但是,的身依活著,尚未。就像迦牟尼佛於菩提下成道之,已一切,但是他的身是留在人四十九年,作弘佛法的工具。又如佛陀的阿弟子,共有一千多人,他於除之後,肉有死,一有冷、、病、痛的果,就是「有涅」。
<2>涅:即是阿於此身死後,不再流生死,一旦,便此不再到世,不再接受任何生命的果;此以後,入寂,不再出。故「涅」。
修四十六行相初果,即入道位,自此而二果及三果,均名有果位。三界惑真之理,登第四阿果位,名位。只有到了果位,方真解自在,才能之入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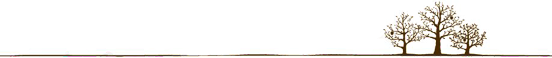
世的苦,是著因,就成,要止息,就要勤修三漏,即能解,也是得到漏通的三修行方式。三漏是八正道的,其中包括了持戒、定、智慧三者,亦即由戒生定,由定慧,由慧起修,分治人的、、痴三毒,最可以解、究竟涅。三者彼此加,缺一不可,而且相相成。只要精修行三漏,必定可以到最的解之道。三是付三毒之法。防非止即戒,戒能伏心;息即定,定能伏嗔恚心;破真叫做慧,慧能伏愚。
佛告弟子:已,今,;已,今,!──三世分的文句,『阿含』中是常的。又如:於不善的,未生(未)的要使他不起,已起(去)的要使他除;善的,未生的要使他生起,已生的要使他增大,就是「四正勤」,修善的精。佛陀示的修持法,是,是,是修,是,直提「下」於三世。不善法,要三世,才不再受去不善的影,引起未的再生。
在『阿含』,佛的契,碓乎流露「三世有」的意趣,如『』卷二:「若所有色:若去,若未,若在;若,若外;若,若;若好,若(作劣);若,若近:彼一切色」。
中於色、受、想、行、,都以去、未、在等,。去、未、在一,、外,、,好、,、近,共五大。在一列中,去、未在,平列而有任何的意味。也是「三世有」的有力教。五,在是最古典的,不同分去理解一切。
《阿含71》世尊告比丘:「云何有身?:五受,云何五?色受,受、想、行、受,是名有身。云何有身集?有、喜俱、彼彼染著,是名有身集。云何有身?有、喜俱、彼彼著,吐,,欲,,是名有身。云何有身道?八道:正、正志、正、正、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有身道。是名有身、有身集、有身、有身道。」
又差者:「比丘知有身、有身集、有身、修有身道,是名比丘欲、等法,修等,究竟苦。…又名比丘究竟,究竟垢,究竟梵行,上士。…又名比丘阿有漏,所作已作,已重,逮得己利,有,正智心解。是名比丘,度,超越境界,防,建法幢。」
云何?:五下分。云何度?:度明深。云何超越境界?:究竟始生死。云何防?:有。云何建法幢?:我慢。」
又差者:「是名比丘五枝,成六枝,守一,依四,,求,,身行息,心善解,慧善解,一立梵行,上士。」其道有三,亦三,有身四,有六。
《阿含388》:「五支,成六分,守於一,依猗於四,除,四衢,想,自身所作,心善解,慧善解」,《增壹阿含46品2》此「所居之有十事」(十者的住所):「五事已除,成就六事,恒一事,四部,劣弱,平等近,正向漏,依倚身行,心善解,智慧解。」《阿含10》:「十解;十居(十者的住所。」:「一者,比丘除五枝。二者,成就六枝。三者,一。四者,依四。五者,。六者,妙求。七者,想。八者,身行已立。九者,心解。十者,慧解。」
《解深密》云:有,一者生起漏智,底除之子,使不再生起,此漏或竟;一凡夫修有漏之六行,相上地下地,而下地之,或抑之行,此有漏或伏。依《俱舍》卷21,所有存在之事物(十八界),由惑可分三,其以道者,所,又作道所、;以修道者,修所,又作修道所、修;如漏法亦可不者,非所,又作非、不。
如何?有四情形,此惑四因。其中,前三者惑之因,後者修惑之因。惑有苦、集、、道等四所之,其四亦各有二,苦、集二下有自界惑、他界惑二者,、道二下有有漏惑、漏惑二者。
(1)遍知─即除惑中之苦、集二下之自界惑,、道二下之漏惑。自界惑,以自己所住之境界象而起之惑;漏惑,以漏法之、道二象所起之惑。此二惑均迷於四理之惑,故若遍知各所(所迷之象)之理,惑即可除。例如苦下之惑,由遍知苦之理而;集下之惑,由遍知集之理而。
(2)能─即除苦、集二下之他界惑。例如在欲界者,以色界等象而起惑,他界惑。他界之惑自界惑之所,故能之自界惑,所之他界惑自亦除。
(3)所─即除、道二下之有漏惑。有漏惑以漏之惑所,故「所」之漏惑,「能」之有漏惑亦自然除。
(4)治─即指修惑唯以治道除之。在九地各九品之中,上上品之惑以下下品之道能治,下下品之惑以上上品之道能治。
十智,指佛法中三乘之者所成就的十智慧,以含所有能究竟果的一切智慧。一般而言,因在佛菩提果解果上的不同,故而有意涵:
阿之十智以解道而言:立此十智,以成就阿一切之智:世俗智、法智、智、苦智、集智、智、道智、他心智、智、生智。
如十智佛菩提道而言,十智三世佛一切智上智慧,令菩勤修,不共所:三世智、佛法智、法界智、法界智、充一切世界智、普照一切世界智、住持一切世界智、知一切生智、知一切法智、知佛智。
生智-梵 anutpādajñāna,巴利 anuppāda-ññāna,指了知一切法生之智。亦即一切,生化之究智慧;於四已自知苦、集、修道、,更遍知「知、、修、」之漏智。又已遍知欲、有、明之三漏及、眠等不再生起,故生智。阿磨集足卷三:「生智云何?如知我已知苦,不知;我已集,不;我已,不;我已修道,不修。此所生智、、明、、解、慧、光、,是名生智。」
此智於位完成,得「智」後,更以一切之道因,果,故非之「得」俱生之漏正智,此唯利根之者能成就。除欲界及有地之外,以其他之四根本定、未至定、中定、下三色定等九地依地。
大乘般若的甚深空到底意味著什的容呢?一切法空,依《般若》的解是:菩提!深者?空是其,相、作、起、生、染、寂、如、法性、、涅。菩提!如是等法,是深。
又言:我不常一切法空耶?菩提言:世尊!佛一切法空。世尊!法空即是不可、有、量、。世尊!空中不可得,量不可得,不可得。以是故,世尊!是不可、、量、。……佛以方便力故分,所不可、、量、、著、空、相、作、起、生、染涅。佛因以方便力。……一切法不可,一切法不可相即是空,是空不可。
一切法的甚深空即是「涅」,是般若所表的。《阿含》起甚深,倍甚深者──涅。般若,空、相、作、起、生、染、寂、、如、法性、及涅等,都是深。寂、、等名,在《阿含》中本都是涅的名,但般若之化法甚深──空之名。不可、、量、等,本都是用形容涅的,在此都用形容「空」。故印法在《空之探究》其《般若》之一切法空的研究而言:之,『般若』的空性,就是「十地品」的「寂分法」,如入,就是涅。明了,『般若』的法空性。是依佛的甚深涅而的。
人所智是自性,藉此所表的深甚「空」,是自性空,亦就是法的自性。但竟智的甚深非一般人所能的,引一般生的契入,故《般若》也到了:「法合和生故自性」。法合和故有自性,自性故空,成了起的自性空。於是《般若》的「空」,便有了自性空世俗的自性空含。《般若》空,集多空,但不出此二。
《阿含》以的佛法,的身心起,指出生死不已的所在,呵斥生死,呵斥,道的修持中得解。解道的中心是起,依起之流所展的便是四。依,尊是(abhisamaya)起而悟成佛的,弟子也依起(及四)而解。但道──四的修持是有次第的,上:「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智」。
修者先了因果的必然性──如知起;依起而知常,我我所,究竟的解──涅寂。所以原始佛教的,便是知四起,得此法住涅之四智。後代一切有部的者更依四十六行相,作漏慧的生起所依。另一方面,智是一的面。智是道之修,一定是倒,罪,的。如光明黑暗一,光明(智慧)一出,黑暗()即。
所以知四的同便有之相之的除。如流果,略三,者惑八十八使。二果薄修惑;不果五下分;四果阿略五上分,者一切。佛法的修持,目的在於解,解即的敷,以的除程度安立果位的次。原始佛教以,所的悟,除了四的知外,的除也是一重。最究竟的是阿,阿一切,悟了最究竟的涅。所的「涅」在《阿含》的定是:涅者,欲永,恚永,愚永,一切永,是名涅。
而阿得涅後,更自作道:「我生已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或作「能自,我生已,梵行已立,所作已作」。《阿含》中,此阿自作,各句之略有,但不外四:1、能自;2、我生已;3、梵行已立;4、(自知)不受後有。在阿含中有很重要的意。因阿一切,失去生三界的因,所以自「所作已」,而且是不再三界受生的,故「不受後有」。也就是:「原始佛教的悟,除了体涅外,『不受後有』也代表著相的意」。
大乘的般若波蜜是信解一切法空,生死即涅。者是先了因果的必然性──如知起;依起而知大,我我所,究竟的解──涅寂。法住智到涅智,由相入到。但直一切法即涅入手的大乘行者,由於方便的不同,因此其深入一切法空,是所的。然,行者真能得果者,也是不著所,不其竟是要入涅的。而大乘的般若空慧不但只是深,且能、,世即涅,不生死,常留世久度生。
菩深入一切法空,知空而能不空的另一原因,是悲所持。於此菩悲力,知空不,三界度化生。悲智本是不同的法,佛法自以,向重智慧,大乘般若法也是如此。不大乘之所以殊,大乘之特色,不只是在流上的解,智慧涵上的。以上菩提目,重於慈悲利他的行,更是大乘佛法的可、殊。以此大悲力,菩否,都入娑婆化度有情。依悲力而入五,使的生法忍菩而言,更出其重要。因此大菩已,失去了生三界的因,唯依悲法性生身,三界以度生。
《般若》的「入」指入涅,重是不再三界、不受後有。般若法的「不」,依《大智度》之包括有意在其中:1、指真的不,未法性,未,故於三界受生身。2、非真不,而是已法性,但三界,不似二乘涅。因此「不」主要是指不三界,是依法性生身或生身而。
文章定位:


 全文
全文